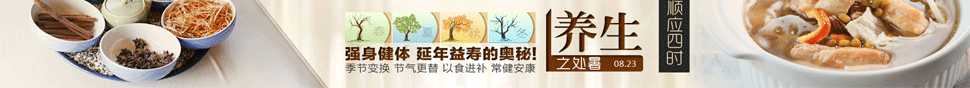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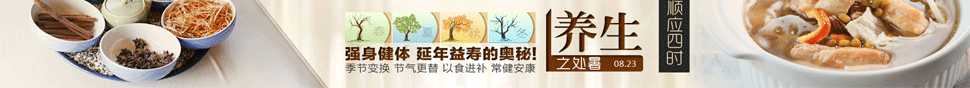
中国画中的开与合有密切的关联性,大到整体构成,小到一枝一叶,起手生发之间的相互照应,都属于开合的范畴。前文形式美当中所讲述的开合呼应,便是“一幅之分”的大开合,此处所讲的开合,他是“一段之分”的小开合大开合关乎龙脉,小开合着眼于置陈布势,两者虽然是两一起的,但是不可以混为一谈,另外,应当个各为所论,也不可偏执一端。清代王原祁曾经在《雨窗漫笔》中说过:“只要知道有开合起浮,而不重视龙脉,就是顾子失女,因此需要两者同时兼顾,不可知知有一不知有二。”中国绘画构图学中如果没有大开合的话,构图就没有了气势可言,难以形成气势。假如龙脉确定下来,具体物象仍然需要布置,所以王原祁继续说到:“并且通幅都是有开合的,分股仍然有开合,尤其在过接映带之间制其有余,弥补其不足之处,使龙脉的正,斜,浑,碎,隐,现,断,续,活泼泼地于其中,方为真画,如果能从此参悟透彻的话,则小块积累成大块,怎么能不接近妙境者乎?”
小开合作与物象的具体布置,要在大开合既定的气脉走势上,顺势而成,上开下合,下开上合,左开右合又开左合,错落有致,方能构成变化。一大一小,一轻一重,一长一短,一高一低,一纵一横都属于开合的范围之內,而开合的前开后合和后开前合,则构或叠压的关系。
叠压有浓淡之分,也有色墨之别,他们是构成中国画二度空间的关系,创造层次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。但是叠压,不仅仅是简单的轻重和墨与色的区别,它的具体落实是要合于开合之理法当中的,它是不能脱离理法而而单独存在的,只有二者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才能使众多的物象相互以为用,井井然而有序。所以这世间之物,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,但是这个规律却不能被打破,一旦破坏则不成系统。
开与合的呼应与叠压的具体布置构成,是要符合中国画结构美的艺术规律,从而以求破除平行,疏密有致,三线交叉,女子交叉最为得宜。当多种线性结构形态交合在一起的时候,切不可以出现中国画结构上讲的所谓忌:“米”字打破现象,这就是要特别强调并加以注意的事情。
开合与叠压同样也是一种呼应的关系,既然前后有所照应,又有宾揖相让,浑然一体。浓淡强弱,动势向背皆皆合于龙脉之势,才是开合变化之道。
然而开合呼应是用以取势,是画面构成的整体运动倾向。开是开放,他是构图着墨的开始之处,合即是合拢,是与开的相互照应。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说过:“分合乃是大字纲也,有一副之分,有一段之分,于此了然,则画道过半矣。”开合有主次,主次分明,开合整而不乱,主次得当,以次辅助主体,使开合相辅相成。
起承转合则是开合呼应的具体运用。是中国画构成的步骤和方式。起是布势的开始,承是顺势而生,起到延续和过渡的作用,转是势的转折变化,是与主势形成矛盾和冲突,变化万千但不伤主势,合则是峰回势聚,取得平衡。起于转为取势而造险,合则是为平衡而破险。在险中求势,在势中造险,以不平衡打破平衡,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,才是取势的道理所在。
交叉叠压就好比枝叶的交叉,如兰花叶的交叉,要有意识地形成不等边的三角形比较反看,不要形成等边三角形或者几何体。我过古代画梅花就要求“女”字形,所谓无女不成梅,画兰花要求破凤眼,就是这个道理画面中有叠压边形成层次,形成藏露的关系,便有了含蓄典雅之美。
开合有主次,但没有定法。开合可以动中有静,静中寓动,以静衬托静,以静衬托动,贵在既然独立,而且又合乎理法,方可法开合之变。所以这开合皆在于画者熟练洞悉理法之后的随心所欲但又不失法度,同时开合也贵在取势。有势则开合既有了气脉,有了走向,同时也开阔了视觉张力。大开大合,气势磅礴;大聚大散,飞扬旷远,但是千变万化最终要归于统一。这不但是取势,布势的规范,而且还是对章法理论把握的深浅,也皆在这其中了。

